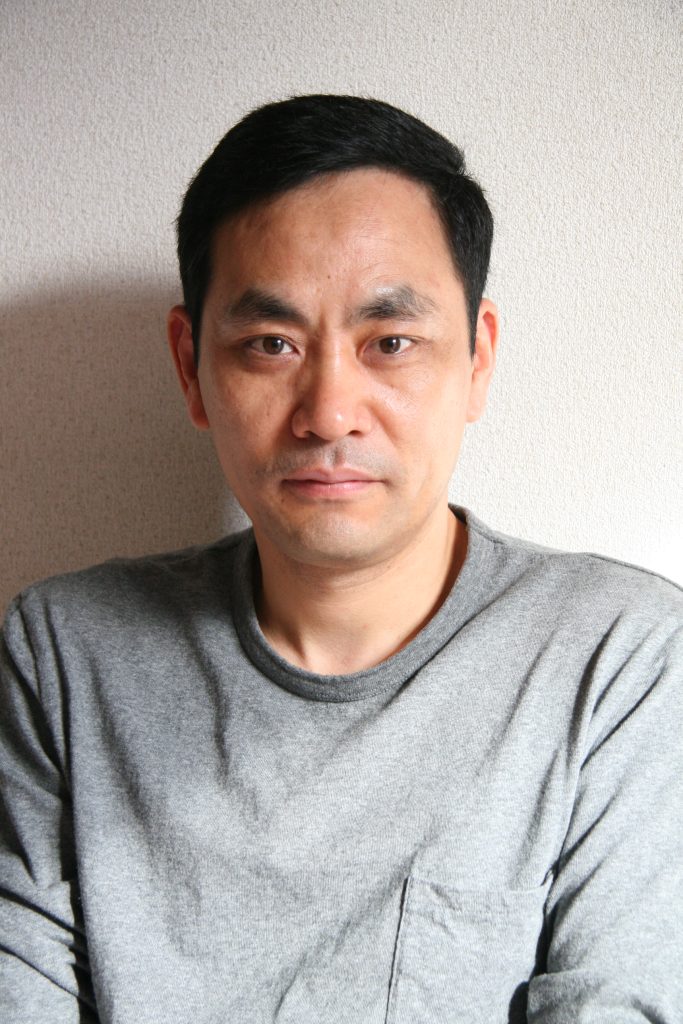■田原
1
毫無疑問,詩人是語言秩序的建立者。
其實,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每一首詩都是詩人內心深處語言衝突的結果。
換一種說法,還可以延伸為:一首詩的成敗取決於詩人語言衝突的強弱程度。
如果只是局限在談論「個人寫作」,而非詩人的「個人寫作」的話,這是一個十分寬泛的話題。外來文化這一概念本身也同樣存在這一問題。
對於在單一母語文化中成長起來的詩人而言,作為外來文化的反義詞——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毋庸爭辯,它既是造就詩人的基礎,也是鑄就詩人語感和意義的母體。外來文化當然同樣也是詩人寫作重要的影響源。
一首詩中究竟含有多少詩人吸收的外來文化,在文化資訊全球化的當下我想連詩人自己都無法說清。文化無國界,詩歌寫作雖然存在語言的局限性,但想像是無限的。
2
寫作遍佈在我們的周圍:新聞報導、非虛構紀實文學、演講稿等等,儘管跟建立在想像和虛構之上的小說和詩歌創作同屬於寫作範疇,但它們在本質上的雲泥之別不言而喻。
就一般論而言,短小精悍、文字有限的詩歌寫作,與側重於敘述和故事結構表現的鴻篇巨制的小說又存在很大的區別。
體裁不同,寫作動機和形象思維的出發點也不同。
作為瞬間和時間的藝術,詩歌寫作帶有一定的神聖性。這種神聖性除了跟詩歌具備對峙、對抗時間和詮釋靈魂的力量外,也跟與詩歌形影不離的靈感、想像、神秘性密切相關。
不僅僅局限在詩歌寫作,對於所有具有創造性的寫作者而言,現代新儒家的早起代表梁漱溟所主張的人必須處理好的三大問題我覺得很值得參考:一、人與物;二、人與人;三、人與自己內心的問題。這三點跟一代大儒季羨林所強調的:一、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二、人與人,包括家庭關係在內;三、個人心中思想與感情矛盾平衡的關係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此,我們還可以聯想起奧地利人文主義心理學先驅阿弗雷德·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一書中所提出的人生必須面對的三大問題:一、我與地球;二、我與他人;三、我與異性。對於詩人而言,有必要還要附加上與語言、與世界、與想像、與歷史、與時代、與平衡、與生活、與自然、與生命、與上帝、與自我、與宇宙等關係。
3
在談論個人寫作與外來文化的關聯性時,在此有必要質問一下什麼是外來文化?
單是從文化的意義來看,不外乎早已被總結過的:a.政治、經濟、地域等方面的文化。b.物質文化。c.精神文明。
就外來文化本身而言,我認為它是各種不同文化相互交匯、碰撞、吸收、融合而成的雜交體。
在此,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日本著名文學批評家加藤週一對日本文化界定的概念:雜交文化。
在一個移民國家或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外來文化司空見慣。
但對一個單一民族、語言相對封閉、文明文化十分落伍的小語種而言,外來文化這一概念是富有革命性、破壞性和解構性的。
從中華文化的演變來看,作為起源於農耕文明而產生的種種文化現象,按照一代大儒錢穆的解釋,中華文化是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且是相對安定的內向型文化。它跟歐洲外延型的、帶有擴張和侵略性的文化大相徑庭。
秦漢、隋唐時期的以狩獵為主的遊牧民如匈奴、鮮卑、契丹、女真,以及後來的元清時期的蒙古族、滿族等等,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文化的衝突究竟產生出了多少新的文化因素,不是這篇短文能解答的問題。
但如果思考一下漢唐時期,西去印度留學修行的僧侶或學者們帶回的佛教經典為中國帶來的文化衝擊,中國文化的雜交性既不難想像,又顯而易見。
中華文化是以固定型文化(農耕)為主,或許摻雜著一定的移動型文化(遊牧)的綜合體。或者說是小麥(北方人)、大米(南方人)和野獸(少數民族)的結合體。
對於歐洲,古希臘古羅馬是最大的外來文化輸出源;對於中國,印度則是最大佛教文化輸出源;對於東亞和東南亞,中國又是儒教、道教和禪宗的最大輸出源。
另外,外來文化的成立與侵入跟翻譯這一媒介有直接關係。
翻譯既是外來文化的橋樑,又是外來文化生產和進口的主要媒介。

4
作為一名遊蕩在漢語和日語之間,用兩種語言來思考和寫作的人,腳踏兩只語言文化之船,不僅沒有使我越過外來文化,反而卻讓我深陷其中。因為無論是母語的漢語,還是非母語的日語,用這兩種文字創作的現代詩,可以說都是外來文化的直接產物。
中國古典詩詞和廣義上的現代詩都是被符號化的一種文化,前者產生於域內,是中國各種文化中一張古老的臉譜;後者來自於域外,是無數外來文化中的一張臉譜。但是,真正的詩歌是超越文化的。
在詩歌寫作中,宗教和信仰有時左右和干涉著詩人的思考和想像,但正像詩歌是超越文化的載體一樣,真正的詩歌最終也是超越宗教和信仰的。
猶太教和基督教中的上帝,伊斯蘭教中的真主,佛教中的釋迦摩尼,中國和日本信仰中的各種神,以及地球上無數被信奉和供養的神靈幾乎都在厲行一種職責——主宰萬物,且都是作為超然的存在而被認知的。但同樣是上帝,在西洋人那裡卻是理性和邏輯的,而作為外來者的上帝在中國人心中卻是感性的,也是經驗和情感中的。有時候我在思考,相對於西方人的罪感文化和日本人的恥感文化,歷史上曾經作為文化輸出大國的中國文化又是什麼呢?我至今仍找不出一個恰當的辭彙,像西方的罪感和日本的恥感一樣來形容和概括中國的當下文化。這種文化迷茫和困惑也許無形地或多或少影響著我的寫作。
5
寫作是詞語的互動過程。
詞語是語言的組成部分。
語言是文化中的核心元素和鏈條。
個人寫作與外來文化的關係其實是個體與非個體的關係,也是我與他者的關係。
這種關係的維繫既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同時進行,又在無意識之中悄悄發生。
在它們之間的互動性之中,雙方都扮演著主動和被動的雙重角色。
隨著互聯網的日漸發達和普及、以及文化資訊的全球化,文化在變得多元鼎立的同時,外來文化的界限會變得越來越曖昧和模糊。某種意義上,文化的曖昧性對純粹的現代詩寫作是一把雙刃劍,從負面意義上說,會對寫作造成尷尬和難度,但同時又存在著為寫作帶來多種可能性和機遇的正面意義。
文化進程的快慢決定著語言的變化和進化速度。
語言進化的快慢程度會對語言的封閉性和開放性直接產生影響。
學習日語很多年後,我才終於明白,我在母語中一直使用的很多現代漢語辭彙都是進口於日本(據相關學者統計,現代漢語裡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辭彙源於日本,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通過對西方各種語言和概念的吸收、消化而發明創造的。其實「母語」一詞也是來自日語)。就是說包括我在內,每一位用現代漢語進行詩歌創作的詩人,每天都在大量使用著日本人發明的漢語辭彙來構築著自己的文學世界,漢語現代詩的想像和詩情、詩風和文體不僅絕大成分是由這些辭彙組成,而且它們還在我們的母語中承擔和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變成了現代漢語詩歌血肉的大量詞語或許是對個人寫作與外來文化的最好說明。
世界上存在一成不變的文化嗎?其實更多的文化是在相互交織、相互碰撞中形成的,就像一千多年前我們向日本出口漢字,一千多年後我們又從日本進口漢語辭彙。
6
文化乃宇宙。
無論是個人寫作還是集體創作,甚或外來文化都不過是文化宇宙中的一個行星而已。
如果把詩人也比作星星,詩人會因為作品的影響力發出不同的光。要麼熠熠生輝,要麼微微閃爍,要麼是模糊的明滅。
詩歌寫作同樣是文化的融合。
因語言文化和生存環境的差異,語言表現、作品風格和詩歌的指向性會略有不同。但就詩歌的本質性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詩歌創作必須超越文化的界限,這一點是詩意最起碼的要求。
田原簡介
田原,旅日詩人、日本文學博士、翻譯家。1965年生於河南漯河,90年代初赴日留學,現為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教授。先後出版有《夢的標點——田原年代詩選》、《夢蛇》等漢語詩集。2001年用日語創作的三首現代詩獲日本首屆「留學生文學獎」。出版有日語詩集《岸的誕生》、《石頭的記憶》、《田原詩集》、《夢之蛇》、《詩人與母親》等。其中《石頭的記憶》2010年獲日本第60屆「H氏詩歌大獎」。2013年獲第10屆上海文學獎,2015年獲海外華文傑出詩人獎,2017年獲臺灣太平洋國際詩歌第一屆翻譯獎等。主編有日文版《谷川俊太郎詩選集》(六卷),在國內、新加坡、香港、臺灣翻譯出版有《谷川俊太郎詩歌總集》(25冊)《異邦人——辻井喬詩選》、《讓我們繼續沉默的旅行——高橋睦郎詩選》、《金子美鈴全集》、《松尾芭蕉俳句選》等詩集,以及小說《人間失格》、《起風了》等。發表有中、短篇小說和大量的日語論文,編選有兩冊日文版《中國新生代詩人詩選》(竹內新譯)等。出版有日語文論集《谷川俊太郎論》(岩波書店)等。迄今已共計出版80餘冊作品集。部分詩歌、論文、繪本先後被翻譯成英、德、西班牙、法、意、土耳其、阿拉伯、芬蘭、葡萄牙語等十多種語言,出版有英語、韓語和蒙古語版詩選集。先後應邀參加法國駐日本大使館舉辦的詩歌之春、東京國際詩歌節、哥本哈根安徒生國際詩歌節、香港國際詩歌節、冰島詩歌節、首爾國際寫作週、臺北詩歌節、上海詩歌節、首屆廣州國際文學節、澳門文學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