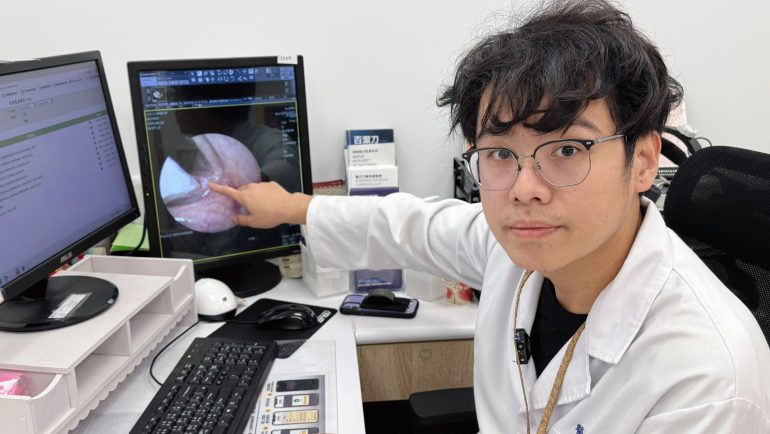A+的滋味
文/冷語妍 畫/徐兆慧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乃歷史上著名的官員和文學家。眾所熟悉他在文章方面,反對晦澀浮華,主張明道致用,史學方面著有《新五代史》,並與宋祁合撰《新唐書》;居官期間,主持過科考,積極提拔曾鞏、蘇軾、王安石等後進,亦竭力支持范仲淹提倡的新政,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樞密副使同平章事。
從事蹟建樹,歐陽修無疑是出類拔萃,可就認識一個人而言,不免刻板嚴謹,欠缺了點趣味,和個人獨特,難得在《美的焦慮》書中,另類展現歐陽修私下醉心嗜好,熱衷收集拓片,撰寫詩話、花譜,人間煙火氣息的一面。
歐陽修熱衷刻字之石,熱忱之深,並不僅只閒暇時娛樂消遣,即使仕宦羈縻,貶謫北方諸路,仍不忘抓緊出京機會,走訪當地山林鄉野,蒐羅石刻。根據他與友人們書信往來,歐陽修豐碩的藏品,除了源於親身四處發掘,有部分則來自同僚饋贈。他們許是知曉歐陽修喜好,也可能是受到請託,在派任國朝各地時幫忙留意。對碑銘的熱愛,在擁有豐富拓片後,歐陽修發揮修史嚴謹,仔細將銘文拓印裝裱,裝訂成卷,一一為每件收藏撰寫跋文,介紹書者生平,探究石刻來歷和內容,並為書法做點評。
以如今觀點,石碑亦是重要文化遺產,鑽研銘文無疑吻合歐陽修大儒形象,然則在他所處時代,這一切卻不那麼想當然爾!並非說時人漠視墨寶,宋代可謂是藝文發展最為輝煌的朝代,書畫名家輩出,一般文人雅士、上至帝王,無不有詩詞字畫雅好,誠如有法帖之祖美譽的《淳化閣帖》,即是由太宗趙光義下詔,授意百官網羅傳世佳作,典藏於宮廷秘閣。
只是如同《淳化閣帖》擇選,偏愛書聖王羲之和王獻之字帖,「二王」在恁時備受推崇,唯有與其飄逸風格相似的草書、行書近草,才被大眾投以關注。對比擇精的鑑賞風氣,歐陽修博愛的品味,相形之下尤顯叛逆。他並不獨好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神光煥然近乎奪目的所謂典範,但凡能讓他感受「怪奇偉麗、工妙可喜」的筆墨,書者籍籍無名也好,佚名也罷,甚至僅存碎石殘碑,都令他歡欣鼓舞,樂於擷納。即便創作非關藝文,只是寺廟碑碣,或喪葬墓誌,又或官府宣告政令,他皆不問出處,兼容並蓄地去收藏它們。
歐陽修將珍藏匯編成一部《集古錄》,為之親撰的目序裡,很是自豪:「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他的收藏時間縱貫古今,囊括上古至唐代,空間橫跨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題材更是包羅萬象,無奇不有。是以朱熹曾直言:「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因為有歐陽修開先河,樹立銘文典藏的標竿,扭轉了前朝偏狹的眼光,促成後世金石學的新興。
然而作為開山祖師的歐陽修,醉心碑刻之際,偶爾卻流露不安。畢竟身為服膺儒家思想的文士,正如孔子所言「敬鬼神而遠之」,歐陽修並不喜鬼神之說,亦鄙薄來自異域的信仰,釋道皆虛妄,每當遇見這類銘文,箇中充斥的異端色彩,見之不懌。偏偏,同一份書文,當他換上鑑賞家的眼光,又覺筆觸新穎,別有番與眾不同的粗野氣息,筆鋒遒勁,不禁為之魅力折服。
其糾結恰呼應書名──美的焦慮。細細思量,這矛盾的名稱頗有意思!欣賞美的事物,應該是輕鬆愉悅,怎麼反生焦慮?其實在歐陽修收藏歷程,不光對物的抉擇憂愁,單就收藏此舉亦讓他掙扎。儒家教育,讚頌的是一簞食一瓢飲,澹泊簡樸生活。雖然在拓片尚為人忽視的朝代,毋須耗費巨額銀錢獲取,但要數十年如一日去保存,並隨他遷徙而轉運,經年累月也是筆可觀花銷,如此一來,與富賈聚斂象牙珠璣的奢靡行徑,本質上何異?豈不和君子寡欲、不役於物,他心中的準繩背道而馳!
一方面是奉行的準則,一方面是摯愛的嗜好,歐陽修左右為難,舉棋不定,魚與熊掌皆不捨。最後他企圖一條折中之道,在銘文裡尋覓史學價值,裨補史籍闕漏,並以聖賢之作為圭臬,效仿其道德精神,使愛好貼近志業,致力雙邊平衡。
亦是在北宋,曾出了位大名鼎鼎的藝術皇帝「宋徽宗」,書畫造詣出類拔萃,書法獨樹一格,筆勢勁逸,意度天成,堪稱驚才絕艷;然而亦是他,玩物喪志,疏於國政,致使社稷傾覆。物本無對錯,文藝本是高雅趣味,關鍵在於把握,佔有物、而不役於物,鬆弛有度,不致縱欲沉湎,而淪落自我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