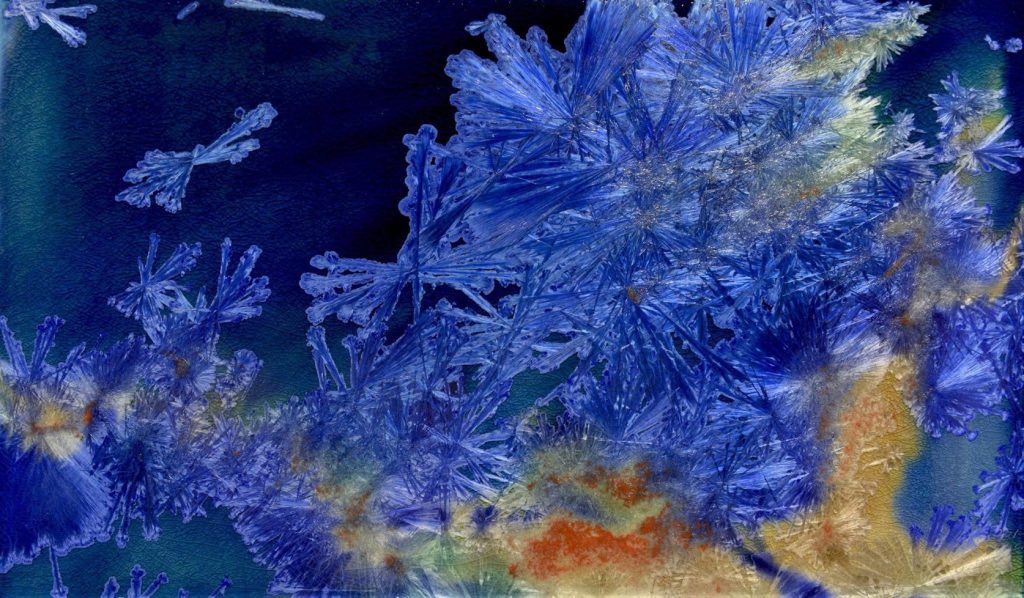多少次,在我童年時分,若我反璞歸真地回頭凝視,多少成人的鬥角勾心,眼神示意,暗湧與推手,奉陪與奉承,在敬酒,在動筷的先後,在輪盤的推動,在狼藉的杯盤構圖間,這些交錯往返的織體:誰為誰反手倒酒,誰看似入口而實則沒有下嚥,誰假意喝醉而大聲喃喃自言。一以蔽之,見山不是山。食物不再是食物,在成人的視角,食物是一個情報互滲的演劇場合,為了展示暴力,或者低聲示弱。而我作為一個孩童,無心於食物,其實,也無心於那些主題,我關心的,彷彿劇場行進中途,一名場記的端茶遞水,彷彿競烈的賽場外圍,一名球經。
在眾人的愛恨角力折衝下,仍然希望自己被喜歡、尊重,像一個狡黠的小孩,本該世故地貼壁而行,戰戰兢兢,盯視此一時空中的精微動靜,將虛實縱深且左右試探一番:他失手摔破的那個碗,是真的失手所丟,還是別有所指?他的笑,他的「唉,怎麼掉了?」,他的目視地面又緩緩抬起頭來看我,他……假作真時真亦假。最後,終於失語再不能反應。
其實,是在僵硬微笑間一瞬自我感覺飄忽,老去。
但那與我何干?與一個懵懂的孩童何干?有關的,因為,我依然樂意動手去接那個破碗,收拾傾溢的湯湯水水,並扶正為他新換的一組碗筷。好像我的內在鏡頭變焦:眼球背後,已經長出了一個世故的成人,將所有算計盡收眼底,雖然外表仍然保持著孩童之姿,孩童的害羞與禮節,孩童呆若木雞地吃虧,還當作占了便宜的颯爽、無所謂。
一直以來,戴著這樣一個小小書僮的面具,在眾人的愛恨折衝下,感到滄桑突然成形,惶懼升起,想要恢復(或湧起)一種冷漠世故以自保,退出劇場演出。但是,當我要將書僮面具摘下時,它已經完全體貼,無法拔除了。
在人生的後青春期,我將計就計,滿足於人生是一場遊戲,你來我往的,或刻薄或輕佻的演劇,究竟是一場不日也散的宴席。在人生的後青春期,慨然平復,依然動心於:去知,去好奇,去置身其中,去推想和料理,去透過自知以知人,透過知人以自知。且永遠無懼於,下一次,再一次。
知人論世,無非是縱使狼狽無言,也不僅止於天真善感地,不倦於知,不疲於世。如果只剩下虛無與厭世,而沒有了好奇,沒有了推想的快樂,沒有了料理的自得其樂,還談什麼知人論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