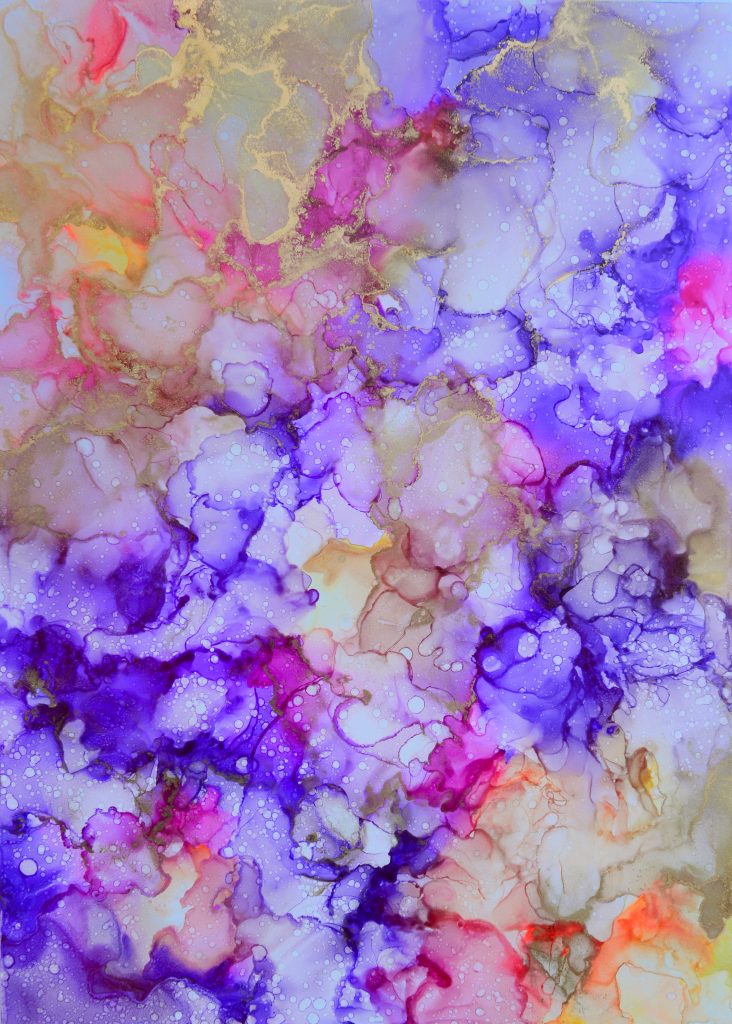這樣說也許不太對,或者說太對了:我一直無法擺脫那股氣味。它像某段被無意掀開的影像軌,突兀地嵌進午後日光與記憶之間。
記得那年夏天,在中山北路那家沒有門牌號碼的同志桑拿裡,我第一次意識到嗅覺是一種比視覺還要先行的慾望地圖。門一打開,是水氣與皮膚交纏之後的蒸餾氣味,有人點了香薰,混著空氣清淨機假裝潔淨的機器音。香氣裡滲進汗與精液的鹹味,一種只存在於那些被社會剝奪命名權的關係之間的味道。我們不說話,只聞見彼此,然後靠近。或者,不靠近。
某個人經過時我突然想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他不是說戀人的氣味比戀人的語言更真實嗎?我相信他。戀愛不是什麼形象或姿態,而是一瞬間那個人身上某種說不清的味道把你整個人拖進他體內。你以為你在談戀愛,其實你只是沉溺在他所散發的那股——怎麼說好呢?——他與你共有卻又無法保有的氣味。
國中時更衣室的那幕場景至今仍完整封存於我的腦中。有人跑完操場回來,衝進狹窄空間,撲鼻而來是黏膩的青春味、乾燥的日光與濕汗的撞擊。身體緊貼過,我沒有轉身去看,只低頭繼續換衣服。但那瞬間——那氣味,我聞見了自己未曾坦白過的祕密。
香水、沐浴乳、髮膠、甚至一瓶來自澳洲的Aesop,都是同志用來構築身體社會性的工具。Le Labo No.33 是某種中產階級的夢——有陽光、有乾淨的書桌、有肌膚與身分證號碼相容的品味。但我總懷疑,這一切是不是真的足以掩蓋那些無法分類的氣味?那些夜市裡混著機油與炸臭豆腐味道的臉,那些躲在公園樹叢間交換擁抱的陌生人?那裡也有氣味啊,只是不上架,也不被命名。
我曾住在一間靠近捷運機廠的出租套房。牆角永遠潮濕,衣櫥裡有件舊吊嘎,衣料吸附著某段早已無法還原的夜晚記憶。那不是愛情,也不是性,只是一種過渡的親密,一種來不及成為事件便已經結束的可能。那味道後來淡了,卻又常在洗衣時,忽然從甩乾的震動中滲出來,像某人輕聲叫你的名字——不是叫你回去,而是提醒你曾經存在。
有一回,我看了蔡明亮的《河流》,其中那場父親與兒子無言相對的戲,我記得的不是畫面,是濕氣。那種水氣,是台北整年都會有的氣味,也是同志故事中無數次出現的背景聲:不是音樂,是一種潮濕裡的潛台詞。
我們談論慾望與身體,但真正說不出口的,是那些穿越我們的氣味。這世界多數人學會了如何用語言編碼慾望,但我們沒有。我們的記憶,總是穿插在某塊潮濕毛巾、某個陌生人留下的被單摺痕之間。
同志的歷史也許不在書裡、不在法條裡,也不在演講稿裡。它可能只是某條內褲上的香水殘留,是某位老同志在圖書館裡翻閱舊小說時,書頁間夾著的煙草味——沒有人記得他的名字,但那味道,我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