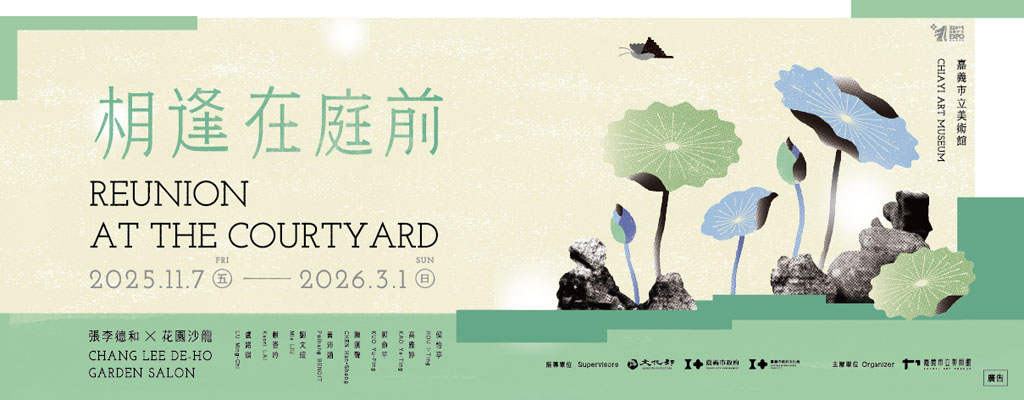文/潘玉毅 圖/黃騰萱

「見字如晤」是舊時書信開頭常用的辭彙。「見字如晤,聲息可辨」,說的是見字如見人、見字如見面的意思,甚至連聲音都清晰可聞。這雖不確然,卻也表達了一種情懷。
書信原有許多種,情書,家書,朋友間的往來唱酬。不論哪一種,在這個資訊化異常發達的時代,收到一封手寫的書信遠比收到一件貴重的禮物更讓人覺得歡喜。
或許有人覺得不屑,微信、短信、伊妹兒那麼方便,何必還用紙筆寫信。殊不知,滿樹繽紛的花朵,可以令人眼花繚亂,卻不抵歐·亨利的那最後一片樹葉更讓人心動而難忘(肖復興語)。這就好比街上各式各樣的禮物有很多,要多精緻有多精緻,在你心裡統統不及心上人給你做的手工製品。
想來,如我一般年紀的人大多有過這樣的情緒:等信的焦慮,收信的喜悅,拆信、讀信時的激動,諸般表情融會在一起,抵得過一幕話劇。
我的書房裡至今仍存放著幾十封往日的書信。這些信裡並沒什麼精彩內容,歸納起來可能就是那幾句話:「你好嗎」、「最近幹嘛呢」、「祝你安好」,可是當這些無關風月的話變成字跡時,就有了不一樣的分量。如今,我已有很多年不寫信了。但閑來沒事的時候,我還是會翻出來看看。每看一次,便好似跟久不聯繫的朋友聊了一會天。
在以前,寫信是很尋常的,因為關山阻越、交通不便,書信是聯繫親人、朋友、情人的紐帶。自古重視郵政,官方有驛站,民間有信局。很多影視劇裡演的巡城馬,便是廣東一帶類似郵差的職業。那時,信函、錢物全靠人手捎帶,巡城馬,便是滿城跑的意思。由於路途遙遠,快是渴求而不得的東西。一封信兜兜轉轉,待傳到收信人手上已不知何時。「洛陽城裡秋風起,欲作家書憶萬重。複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因為音訊難通,寫信的人恨不能把自己的滿腹柔情都寫在紙間,可是想說的話太多了,不知從何說起。與過去不同的是,時下卻有一種慢信。有一年我到西遞遊玩,在古鎮裡看到如許文字:「一封信,沉澱了時間,留給多年以後,來自曾經的你;一面牆,帶你穿越時光,在古樸的西遞寫下一張明信片,一封信,寄給未來的你/TA。」一封信在當時寫下,卻在很多年以後收到——這種感覺,說不上多有詩意,但別有一番回味。
寫信是一種情懷,讀信是一種享受。梁實秋就書信有過這般形容:「家人朋友間聚散匆匆,暌違之後,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憶,有所感,不願獨秘,願人分享,則乘興奮筆,借通情愫。寫信者並無所求,受信者但覺情誼翕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此語甚是精妙。譬如你看到一處美景,用細細的文字寫下來,寄給朋友。朋友打開你寫的信,便似你在他身邊講故事給他聽一樣。若是換作現代人常用的方式:拍一張照片,傳給朋友或者傳到朋友圈,得一個點贊或者得一句「真好看」,就沒多大意思了。
鴻雁傳書,信是載體,在信裡,裝著的思念常常超重。紙短情長,意在言外,寫信的人懂,看信的人也懂,這便是「見字如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