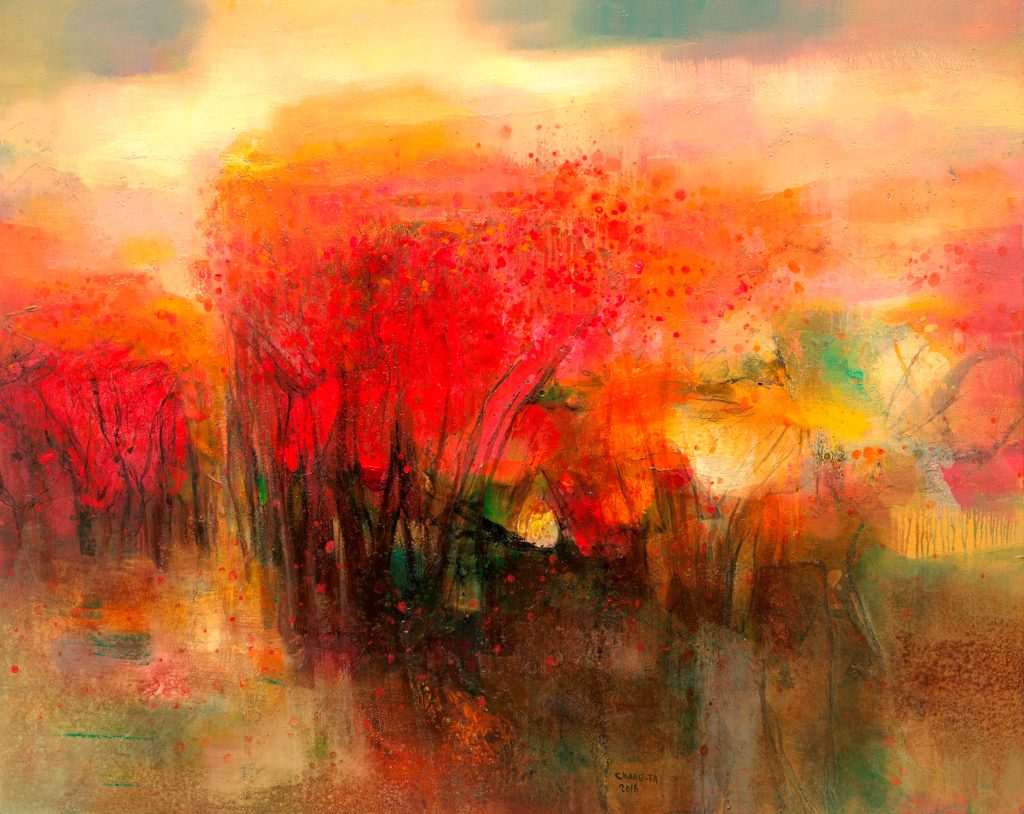
文/陳銘磻 畫/簡昌達
花色褪盡亦藏舊
《以父為名》、《父親》——淚光閃閃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晦秋,猝然斜風細雨的新竹,我喊叫爸爸的父親,在省立新竹醫院病房,因急性呼吸衰竭和慢性阻塞性肺炎併發,斷氣往生;我在接獲緊急通報,趕赴病榻不見身影,黯然神傷穿越淒風苦雨的陰森太平間,叩拜他的離去。
一切靜寂無聲,跪拜的那一抹愁容,竟成父子終必永別的讖語。
父親生前從事新聞工作,疼惜子女,我卻從未細述他的生平事蹟,棄世後,發願用一年時間,記錄與他親子共處四十餘年的苦樂時光,打算在他周年忌辰焚書天國,請他過目,讓他知道,我有多想念爸爸。
人生翻湧無數愛恨別離,父親棄世數日,我從新竹返回台北,和時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許悔之通話,央託他能否在父親出殯日,刊載我的疼心泣血之作〈民國清朝〉,我打算購買三百份當日副刊,發送給親往追悼會場的親朋好友,作為悼念。他理解父愛浩蕩,恩重如山,同意我的無理請託,寬慰不少我凌亂不堪的心緒。
發表敘述出生日治大正,成長台灣、大阪,名字卻叫清朝的父親的〈民國清朝〉後,我打定主意要把寫作這件事當職志。然,每逢提筆,心情必定掉入無法自抑的痛苦深淵,不想寫,因為每寫必涕泣,彷彿要流乾所有淚水;深夜獨坐封閉的房間,明明無風滲入,卻覺背脊發涼,感覺他正以隱然之姿現身,探我寫作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他似乎未曾離開,對著我說,你可以的。這句話就這樣伴我走過五十年的寫作時光。
始終不願面對父親離去的現實,翌年,寫作完成《以父為名》,如願焚燒至天國,父親看見了嗎?我心多沉重。
《以父為名》出版八年後,轉由李錫東主持的宇河出版社,增訂重版,何南輝主編,取名《父親》。詩人吳晟賜序寫道:「可以想見阿磻寫作過程,強忍著多大悲傷,多麼綿密的思念,這樣的悲傷和思念,則深深感染著讀者。」又說:「篇篇首尾相互呼應,更發揮了綿延不絕的情感傳達。」
二0一六年夏,接受台語文學者鄭順聰在教育電台主持的《為台灣文學朗讀》訪問,事後,他把訪談寫成短文,適切說出我與父親,親密、友善的關係:
父親是他的偶像。
銘磻老師說,父親從未對他疾言厲色,一絲絲都沒有,他們的關係猶如兄弟那般密切親近。
有一次,他跟媽媽口角,負氣離家出走(都是要表演給長輩看的),跟著同學坐車到新竹橫山的客家夥房,離新竹市的家非常遠、非常深山。
那是個極為安靜純樸的地方,同學的爸媽也沒問,他也沒通知家裡,就住在那兒,無比地闃然寂靜。
夜半,狗狺狺吼叫,他跑出夥房外,看著遠方有台摩托車,頭燈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停下車,是父親,沒有生氣,就把他帶了回去。
那個時代,交通與通訊都很不便,陳銘磻疑惑,父親是怎麼找到他的?
父親不說。
臨終前,陳銘磻再問了一次。
還是不說。
是解不開的謎,是濃得化不開的親情。
好比夜晚的明月說:「我一直都想被你看見,所以才努力發光。」人不都是為了被愛而活著!用依戀追懷一閃而過的美好記憶,不然,人世間還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別讓父親知道我在落淚。人生各有各的辛酸,被孩子冷落的心情最寂寞,承續父子二人一生的苦澀與榮耀,《以父為名》、《父親》出版迄今多年,始終無力翻閱,目不忍睹,每讀必泣、必淚,只因他是永世父親。
不過比你們早幾步來到人間
《我家有對雙胞胎》——長工日誌
我出生在鄰里口傳書香門第的家庭,父親是日治時代有能力到大阪求學的青年,回台後,捨棄教職,選擇熱愛的新聞工作為職志,熱心公益,疼愛子女,生就一副好心腸。猶記小時,每逢下雨過後,總會帶領子女到街坊做修路善事,他是一位好父親,也是典範,我喜歡跟隨他做事兼當遊戲玩,發願有朝一日也要做個像他那樣疼愛子女的父親。
婚後,養育了一個善解人意、才情洋溢的女兒,多年後,慶幸老天恩賜,送給一對孿生子,父親歡喜,身為人子人父的我更喜歡。
寒流來襲的隆冬降臨人世的孿生子,進入原本只有三口的人家,我既有的生活態勢,像無風不起浪的天候,變化多端,憂喜苦樂的日子都變了樣,樣樣都成日常話題;我常趁勞累工作之餘,空出時間,記錄他們0歲之後的成長花絮,為了避開兩個不解寫作辛勞的男孩的破壞行為,定時嚴禁兩人進入寫字間,對我來說,要求歸要求,哄、騙,無一成效。忙碌的日子,身為陳家長工,又得偷閒寫作,一樣不得安寧。想來,打算為文敘說一對使人頭疼的孿生子成長的《我家有對雙胞胎》,寫作過程必定備嘗勞苦。
時刻告誡自己:人生都是自由的,即使是一家人,也應當適時做一個旁觀者,身為人父,就要學我的父親疼愛子女那樣,不隨意打罵;可是父親沒有雙胞胎兒子,我這個笨父親卻有一對頑皮不馴的雙生子,怎麼辦?我的兄長,導演梁修身給這本書的序文說:
這有趣的孿生子家庭在銘磻筆下,失序中帶著迷人的多姿色澤,我見孿生子如見思維細膩的作者,在混沌的成長過程,演繹一段家庭倫理悲喜劇,果真是孿生子家族「辛酸血淚」全紀錄,正如我熟識近五十年,寫作未曾輟斷的銘磻在書中勉勵孿生子:「我畢竟有堅毅的信念認定,善良的人,只要一心想著做好人,準有德惠。你心良善,必得厚福。」笑中帶淚,淚眼清明,這本父子親情書值得細讀。
作為雙生子的父親,向來被禮讚「老師」,美譽「作家」,也沒多大了不得,我不過比大家早幾步來到人間,財富無半點,學問沒多高,為雙生子取名,不依恃傳統,筆畫越少越好,那就「陳一、陳二、陳三(或陳雷公)」,可以嗎?父母笑我腦筋壞去,讀書讀到外太空。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責任人,人的出生是為了見識和聆聽這個世界的樣態,就算最終沒能成就什麼,我們呀,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活下去的甚美旨趣。就像寫作雙生子成長的《我家有對雙胞胎》,取其生活趣事,是作為父親的善心好意,或能獲得些許理直氣壯的心安理得;而人生終究該如何收山?想說的話,直到如今仍無法脫口說出,那就寫成短箋,記在這裡,作為囑咐:
我應該要走的,人生終歸孤單一場,消逝是必然,如果有一天我走了,請不要傷悲,能陪家人走一段長路,偶而在每個人都可能迷失一時的生命旅程,輕巧撥開迷霧,已夠心滿意足,不想說是責任完成,確實也夠盡責。
時間會不勞心力的處理我離開後的一切,禍福無常,憂喜難定的日子過去後,你們會淡忘這件事,人們甚至會遺忘我這個人,這是生命法則的最後現象。不彼此叨擾,該是成年人不必言明的默契。
多數時刻,人會老去得悄無聲息,我常是一言不發的低頭趕路、埋首工作,雖然如願寫作出版了一二0本書,稍稍達成我父在世時,對我的期望,若覺無法持續下去,便是此生最大遺憾。
喜歡我家小孩,喜歡逐漸長大的孫女樂樂,活潑、懂事、大方、窩心的舉止,為陳家帶來勃勃生氣,她的爸爸,雙生長子請繼續培育樂樂快樂成長。
如果有一天,我必須遠行,請雙胞胎照顧媽媽,她承載我過重過多的少爺脾氣,難為她忍受那麼久;她處世雖笨拙,卻是疼惜孩子的母親,她其實是孤獨的,所以才會常常把話說得如此鬆散,我走後,她一定會這樣說:一個人也能活下去。
如果有一天,作別塵世,請家人彼此相愛,彼此照應,活出堅忍骨氣,我的後半生沒能力留下貴重財富,對不起,是個失敗的父親,只能託付姊姊費心處理往後的事了。
我的一生孤寂,卻過得充實,今天的事會成為明日的記憶,明天的記憶會沉埋在消逝的歲月,一併消失的還有我的名字和樣子。人生未盡時,衷心感謝親愛的女兒,在二十歲之後,對我寫作日本文學地景助益良多,我喜歡妳關愛家人的熱忱,多年來,妳所有的付出,都像是來給陳家報恩。相逢有時,人生終須一別,感謝你們願意出生作為陳銘磻的家人,感謝你們伴隨勇渡漫長的艱困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