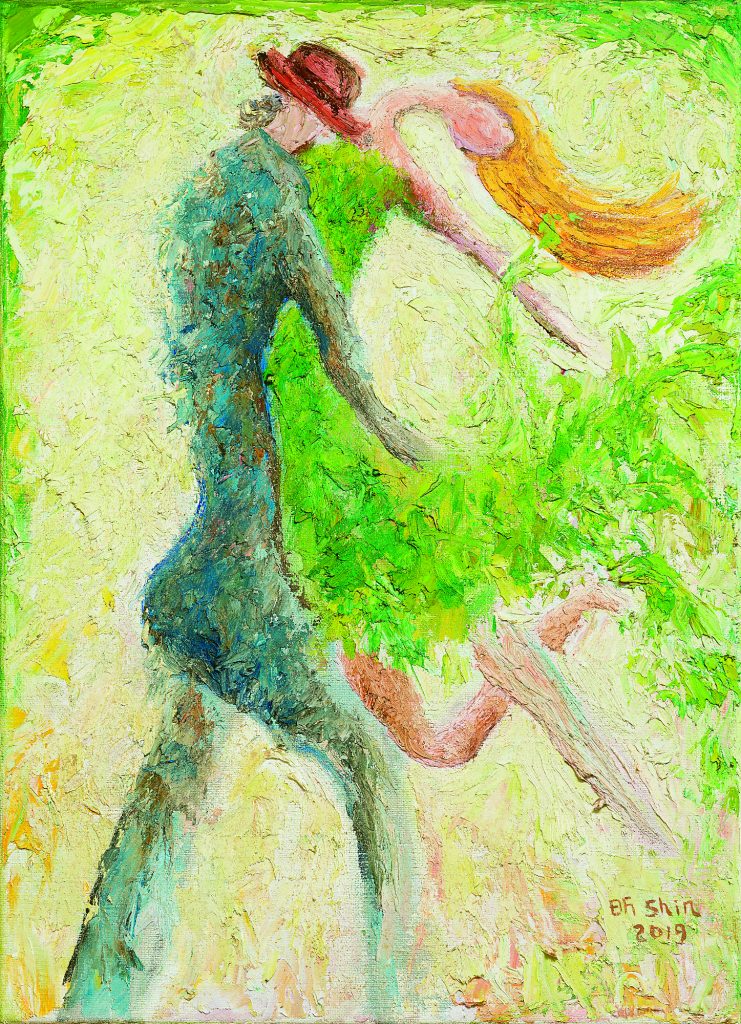媽媽緊握方向盤的指節泛白,我爸坐在副駕,揮舞的左手彷彿擋風玻璃前的第三支雨刷,伴隨高分貝聲量——「太靠近中線了,車距維持好,沒打方向燈、馬路三寶哦你……」媽媽將車子緩緩駛向路邊白線,彷彿被迫靠岸的舟。過往幾次替媽媽幫腔的不好經驗如倒車鏡裡急退的風景,於是我安安靜靜地待在後座。
爸爸在中學教書三十年,下指導棋落子成癮,只要坐上家裡的車,不論他是正副駕駛,他眼裡的世界頓分成二——車速比他快的瘋子及比他慢的菜鳥。夫妻倆家中爭執時尚能退守不同房間,車內鐵皮籠罩的狹窄密室卻無處可逃,兩具困在皮囊裡的倔強個性,在對話句逗或轉彎處伺機而動。
媽媽四十歲時調職,通勤路上騎車需半小時以上,蘭陽多雨,路途蜿蜒,機車後視鏡裡經常是灰濛濛的天。某大雨早上,對向車燈在她左肩烙下怵目擦痕,全家力勸她去駕訓班考照。此後,週末時間,車子駕駛權才「被迫」還給我爸。我待後座,在補習班的往返途中見證了比工作上課的週間日更緊繃的氣氛:他倆爭奪方向盤與生活航道的掌舵權。
從爭吵的碎片裡,我拼湊出往昔曾有的畫面:機車後座圈住前方腰身的手與隨風揚起的絲巾,火車座位交疊的掌紋,當年那個認為女人要獨立、不必依賴別人接送的男人,如今卻懷疑起太太當司機的能力;每當我爸微醺由我媽代駕,正副駕視線的落差,常錯估我媽與來車的距離而語出責備,路人經過,也許以為他倆是駕訓班的教練與新手。
媽媽納悶為何駕駛時沒有我爸同車,反而開得更平穩,能輕鬆自在觀賞風景、聽音樂。她的心理諮商師好友說這是信任機件失靈——我爸質疑我媽的駕駛技術,媽媽則狐疑指揮的正確性,那些深埋在日常溝壑裡的溝通失調與不信任等地雷,便在油門與煞車間接連引爆。
我記得那些時刻:當爸爸精神不濟、由我媽駕駛時,她按下示意超車的閃燈,衡量何時加速前進,我爸常嘖聲連連;當媽媽評估倒車距離,想嵌入前後車輛騰出的空位,爸爸的喉結總會頻繁上下滾動——那是他將怒氣往喉裡吞嚥的動作,然後一聲雷暴:「到底行不行啊?」她行的,只要他安靜。最終噤聲的總是媽媽,爭執會讓她開車分心。
獨駕時的媽媽是另一種存在:右手不必恪守先生規定的三點鐘方向,可以自在擱淺於五點鐘位置;中廣「健康 ON AIR」頻道流洩著藥學博士的嗓音——這是我爸嗤之為沒有科學根據的節目。媽可以輕哼歌曲,我爸在車上時素來聽政論廣播。偶爾我爸微醺由我媽代駕,開車過程必須接受聲控指揮:「減速啦,快撞到了,行不行啊?」她曾揣測先生是不是連人生的方向盤都想接管?我勸道把那些指揮冥想成空白頻道的雜訊,然而有些聲音已經滲入骨髓。
我想起家裡的日常,事情無論大小,爸爸都想軋一角。我家空間不大,為了不讓孩子受影響,他倆後來學會在車裡延續未竟的「討論」:例如媽媽想培養孩子的音樂素養,爸爸認為學音樂浪費時間金錢,後來弟弟中止的鋼琴課是我媽夢想的斷弦;又如我遺傳到母系的嬌小身形,成了爸爸親族聚會時反覆拿出談論「冬瓜基因」的笑談,媽媽因此想減少回老家的次數,然而未果。媽媽是職業婦女,戶政機關常有民眾投訴服務不周、效率慢,她經常在主管辦公室與民眾申辦事務櫃檯間反覆傾軋,週末還得隨我爸駛向宗親密佈的老宅省親。爸爸在十五個手足間排序七,親族聚會首要目的是炫耀小孩,偏偏我家這脈極是平庸。會不會因為如此,那四輪方寸間的自主權才令媽媽倍覺珍貴。
某個補習歸來的夜,我提及閱讀測驗中佛洛伊德「夢的解析」,媽媽忽然說起重複的夢境:煮菜時不小心切斷五指,指頭在送醫途中不慎遺失,醫生說若在五小時內找到便可接回去。醫院時鐘滴答作響,媽媽急得拜託全家幫忙。我爸翻箱倒櫃,最後在垃圾桶發現一只生鏽鐵盒。手指會在裡面嗎?但盒匣鎖住,需要鑰匙才能打開。媽媽心念一動,要爸爸拿出家中鑰匙一一測試,當鎖孔與汽車鑰匙嚴絲合縫的瞬間,喀喇聲響驚醒長夜——肉色手指靜臥其中,卻已錯過了縫接時間。
如今雙親髮色漸霜,爭執仍如例行公事。我爸始終學不會放手,也許我媽還有一段尋指之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