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
1
在這個時代,詩歌還有什麼意義?
道可道,非常道,同理,詩歌要是能說出一般程度上的「意義」的話,似乎也就不是詩了;換句話說,詩之所以是詩,是它不囿於普通意義的「意義」,詩可以徹底的非功利化。
但這不應該成為詩追求無意義的藉口,詩可以無意義不等於詩追求無意義——即使無意義的詩本身它的存在也是一種意義,尤其當它處於一個事事都被追問意義的功利時代之時——但炫耀「無意義」則又成了急功近利的終南捷徑了。
無意義之詩表明自己的超越性的意義,倒也是對時代的一種反詰、甚至反抗:比如說詩把語言從日常功能性中抽離出來,彰顯了語言本身的美與根源性重生,這就是一種民族精神的重建;詩把被時代否定的價值如慢、空、敗、逆、負等等予以強調,是一種對整個世界的簡單二元化的不滿足,從非理性非邏輯的思維空間給予我們省思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
詩無意義,又是最多意義的。
2
詩,首先是自由的,其次才是好或壞的、美或醜的。自由不應該成為討巧的托辭,因為我們也應該記住:自由有其驚險的代價,或者說,越自由,詩的難度越大而不是相反。
沒有人身自由,人仍能寫出好詩;但沒有對自由的嚮往,對自由的執著,絕不能寫好詩。
詩是一條恆久不息的大河,不存在斷裂。
「理論蒼白,而生命之樹長青」,不懂這一句的創作者,再有才華和智力也枉然,在詩之道上會鬼打牆、循環迷失。但若一味向生命提款、成為個人可憐經驗的自我獵奇者,或者嗜痂炫傷者,最終也會停止在自瀆的無聊,即是另一種蒼白。
詩不只有好壞之分,更有有可能性的詩與扼殺可能性的詩之分。因此我最終還是會選擇自由詩、開放詩,而不是格律(包括形式上的格律以及頭腦裡的戒律),我希望我與年輕一代詩人更多寫未知的、實驗的詩,雖然可能會失敗,但比一切勝券在握的寫作操練、批量生產要有意義得多。
詩作為文學當中最具游擊、機動性的尖銳文體,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任性」,去試探文學與精神的邊界,做最極限的外推。這一點不只是著眼於超現實主義或狂想性質的文學,同時也適用於歷史與現實的處理,詩可以充當破壁者、挑釁者甚至異端,在面對擁有多種面具的歷史、與荒蠻無理的現實之時。
詩人是無法饜足者,他對當下已有的意識形態也好、文化立場也好、文學範式也好,都不可能僅僅從中做出選擇。於是,詩人創造,雪萊意義上的詩人乃立法者,便是這個意思。在創造的過程裡必然有大刀闊斧有泥石俱下,青年人們(以及所有仍有青年之心的詩人)不要懼怕冒犯什麼,不必有得失心,須知赤子乃是赤裸裸奔跑在真理之荊棘中的人。「運偉大之思者,必行偉大之迷途」,這是海德格的名言,我希望真的是這樣,祝福我的詩友和我自己,要對得起我們現在走的迷途。
大多數詩人寫詩的初心、出發點都是非如此不可的表達之緊迫感所致,但漸漸的隨著名利的介入、技巧的純熟,很多詩人就會因循自己的成功模式而造詩,更甚者是根據「場域」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的本意,寫「受歡迎」的詩——其實這無關現代主義與後現代價值取向之分別,而是寫作者自我定位的高下,也就是說你是否在乎詩的尊嚴和純潔(無邪)。
在乎,廣東話叫「志在」。志在的志,就是詩言志的志,我希望這樣任性地定義。甚至「意志」,乃是以意象重現我們的志,是詩人的能耐。
詩,言說那些我們在乎的東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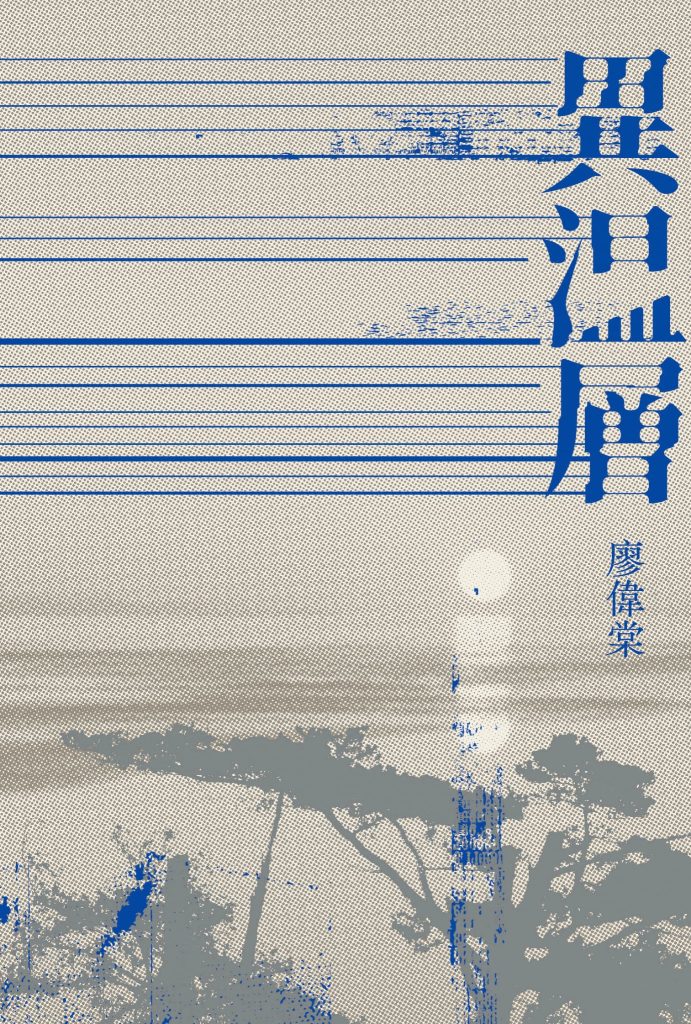
3
詩為詩人個人而寫,但個人要做好這個時代的個人,個人要成為最敏感的試紙、探熱針、實驗品,這樣你書寫自己就是書寫這個時代。
詩為他人而寫,但詩在塑造它的讀者,要求它的每個讀者都成為上述的個人,然後詩不設限,在他人心中重寫一次變成一首新詩。
詩人與詩的關係是互為因果的,做好一個人才能寫好詩,寫好詩能引領你做好(完整)一個人,詩中的詩人形象真正會成為一個詩人的自我。
詩歌語言必須負起對傳統語言的招魂和換血的使命,它應該置身於民族語言的過去和未來之間,提醒兩者的對話,成為兩者的回聲。它還應該成為重建人民的想象力的魔術棒,使他們逃脫、甚至反抗功利話語的奴役。
詩的力量在於讓你面對虛無、權力、毀滅等龐大實物時沉得住氣,然後「沉而能飛」(顧隨先生形容杜甫的話)。
詩不要撒嬌,甚至不要以詩人所遭遇的殘酷來撒嬌。詩要做到不卑不亢,才能贏得尊重。
華文現代詩自救之第一要務是:不打妄語。做不到這一點,多聰明都沒用。
很多你驟眼看起來很不錯但不知所云的詩,其實不是詩,是一種腔調,它不斷呢喃,把讀者和詩人自己都催眠了,暗示他們:這是詩,這是好詩。而且壞詩人們達成共謀,以劣幣驅逐良幣。
一首詩不只是音樂,而是「音牆」和「弦外之音」,不只是建築,而是「家」和「教堂」,不只是織物,而是「刺繡」和「旗」。
我十年前寫龐德的一句話:「直接,明亮,響亮,自信,清澈。他的諷刺也是用歌唱的方式完成的,所以遠遠高於諷刺對象和諷刺本身。而他的雄辯,包含悲憫。」後來也成為我寫詩的座右銘。
詩與大眾的關係是一回事,詩人與大眾的關係是另一回事,舉個例子:一個文學院裏的卡夫卡永遠成不了奔忙於訴訟與城堡的K,成為了土地測量員K才成為卡夫卡。
詩是魔術,但詩人不可以魔術師自居。
4
詩是超越的,也是邊緣的。
其實對詩人來說,不存在上升或者下降的問題,只有要麼一切和要麼全無的問題;因此詩人難以固定成為星座,他們不由自主地成為流星或者彗星。
詩如果是尖端,這個尖端不一定是巔峰,也可能是向下的一個至深的極點。
這樣的「詩是個有機體或一部時間機器,從一開始就努力達到終點。」意大利哲學家阿岡本說。
這樣的詩是對未來的考古,也是對過去的科幻,我們的預言是重新發明已經消逝的東西。因此詩人永遠年輕,也永遠和土地一樣蒼老。
二十一世紀過去了二十多年,我們都彷彿生活在我們小時候想像過但是想像不到的未來裡了,但有人在考古。這就像十九世紀詩人王爾德說的:我們都生活在溝渠中,但有人仰望星空。
這是不合時宜的。而我們正是以我們的不合時宜的詩文字、不合時宜的對文字的態度,來幫助我們親近真正的現在——
這個矛盾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