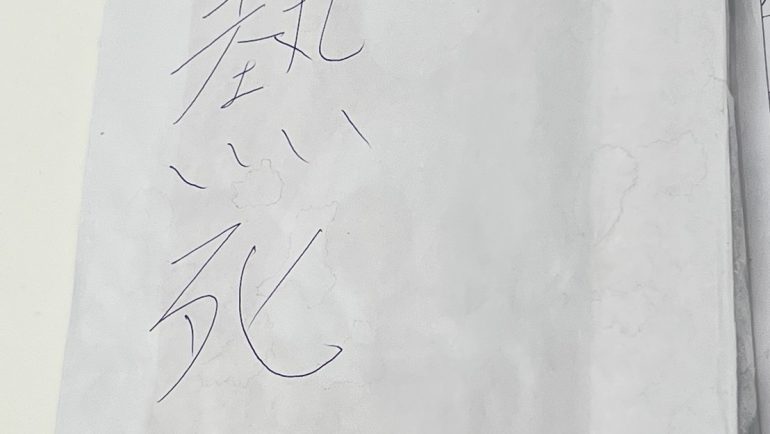從史前祭祀到清宮收藏,古玉如何在誤讀與再詮釋中展現文化的多重生命
劉振漢
作者介紹:劉振漢先生現擔任台南文物協會副理事長,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碩士班」畢業,收藏方向主要為古玉器範疇。
一、引言
在中國古代文明的長河裡,玉器始終扮演著獨特而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裝飾之物,更是宗教、政治與文化的載體。從史前社會的祭祀儀禮,到帝王書齋中的文房雅玩,玉器的意涵雖隨時代而變,卻始終承載著權力與文化的象徵。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文化形態,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的關鍵一環。
筆者曾在〈解碼五千年:玉雕紋方鐲的前世今生與誤解〉一文中,談到乾隆皇帝見到一件良渚玉琮時,誤認為輦車的承重器,並刻詩題咏,使其意義在流轉中發生轉換。那件器物的遭遇,見證了歷史記憶的遺失與重建。本文希望延續這個主題,藉由另外兩件同樣出自龍山文化的玉圭形器,來比較它們的特徵,並探討古玉如何在歷史長河中可能被誤讀與再詮釋,最終展現跨越千年的文化生命力。若讀者有興趣也可將筆者所寫的〈從故宮的一件龍山文化的玉圭談起〉一同閱讀。
二、龍山文化與玉圭形器的原始意義
龍山文化發源於黃河中下游,是中國史前社會進入複雜化與階層分化的重要階段。這個時期,除了舉世聞名的蛋殼黑陶外,玉器的出現與精緻化,也揭示了權力象徵與宗教祭祀的制度雛形。
本文所稱的「玉圭形器」,是指龍山文化時期出土的長條形玉器。其形制與後世《周禮》所載的「圭」相似,但實際上更接近早期玉鉞的雛形。「圭」這一名稱是後世沿用的稱呼,方便對照理解,嚴格來說並不代表龍山時期已經存在制度化的「圭」。
圖一:龍山文化玉圭形器,器形修長,刃口平直,長21、寬4.9、厚0.7公分,1976年江蘇省潥陽市出土。
三、兩件玉圭形器的相關特徵
第一件玉圭形器
故宮博物院定名為「玉鉞」,長18.7公分、寬4.53–5.4公分、厚1.3公分,材質為細膩不透明的牙白色玉。全器呈長梯形,刃口平直而鈍,無明顯使用痕跡。特別之處在於有兩個圓孔:一個貼近柄端邊緣,單面鑽成;另一孔較大,採對鑽而成。孔的設置或與佩掛或固定方式有關,但確切功能至今仍未解明。
圖二:第一件玉圭形器,配有絲穗、紫檀木盒,並將御製詩刻在玉上。
第二件玉圭形器
故宮博物院定名為「玉圭」,長31.1公分、寬8.5公分、最厚1.25公分,材質為牙黃色閃玉。器形窄長,刃部同樣平直無痕,僅有單孔,孔壁平直,展現出高超的鑽孔技術。尺寸較大,視覺上更具威嚴感,或許在當時屬於更高階層或特定場合使用的禮器。
圖三:第二件玉圭形器,器表除了加刻御製詩外,還刻了乾隆皇帝的四個璽文。
這兩件玉圭形器雖同屬龍山文化,但在材質、大小與孔的設計上各有差異,正說明了玉器製作的多樣性,也可能反映出不同功能與地位的差別。
四、乾隆皇帝的再詮釋
這兩件玉圭形器的故事,並不僅止於史前時代。它們在清代被乾隆皇帝重新認識,並留下御製詩刻,讓我們看到古器物跨越時空的「再詮釋」。
第一件玉圭形器的解讀
乾隆曾為之題詩〈題古玉斧珮〉,詩中有言「玉寓潤温斧寓剛,古人作珮意誠良」,可知乾隆皇帝認為這是古人以玉所製作的斧形佩飾,象徵剛柔並濟。器表刻有御製詩與皇帝璽文,他甚至為此配置絲穗、紫檀木盒,並在盒內加刻御製詩,可見其珍愛之情。
圖四:第一件玉圭形器上乾隆御製詩及璽印
第二件玉圭形器的解讀
乾隆曾兩度為其題詩〈題古玉尺〉、〈再題古玉尺〉,將其誤認為「玉尺」,視為丈量用具。器表刻有御製詩與皇帝璽文,並加以木托與絲穗陪襯。乾隆的理解雖與今日考古研究大相逕庭,但這些「誤讀」卻正顯示了不同時代對古玉的再詮釋與想像。
圖五:第二件玉圭形器上的乾隆御製詩題刻
五、文化意涵與歷史啟發
從龍山先民的手中,到清宮帝王的收藏,玉圭形器歷經數千年的文化轉化。它原本的宗教與權力意義,在歷史流轉中逐漸模糊,反而被後人賦予新的解釋。
這提醒我們:考古器物並非靜止不變,而是會隨著時代的知識結構與審美趣味而「重生」。當我們閱讀早期考古報告時,也常有類似感受—因為某些器形早已淹沒於歷史長河,後代早已不知其所以。乾隆的詮釋雖不正確,但卻折射出古玉在清代宮廷中的文化價值。對我們今日而言,既理解玉圭形器在史前的本義,也多了一層乾隆皇帝對它的文化再造的思考。
六、結語
玉圭形器,是龍山文化先民凝聚智慧與信仰的結晶。兩件玉圭形器,一大一小,一白一黃,見證了新石器時代玉工的精湛技藝與社會象徵。同時,它們也承載了乾隆皇帝的再詮釋,跨越時空,成為清宮文化的一部分。
圖六:兩件玉圭形器並列對照圖
圖片來源
圖一:南京博物院編,《玉潤中華:中國玉器的萬年史詩圖卷》,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頁100。
圖二、圖四、圖六:玉鉞。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圖三、圖五、圖六:玉圭。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CC BY 4.0 @ www.npm.gov.tw
作者的話
乾隆皇帝曾將良渚玉琮誤解為「輞頭」,亦曾錯讀龍山文化的玉圭形器。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些並非不可原諒的錯誤,而是特定時代條件下的必然局限。正因他對古玉懷有極大的熱情,才推動了清代玉器收藏的蓬勃發展,並開啟了玉器藝術的另一個輝煌時代。更耐人尋味的是,即便身為帝王,手握整個帝國的資源,身邊聚集無數飽學之士,仍無法完全洞悉古玉的奧祕;那麼,今日的收藏家與研究者又怎能自詡無所不知?因此,我們更應承認人類理解的侷限,唯有在持續的學習與探索中,方能一步步逼近歷史的真實。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