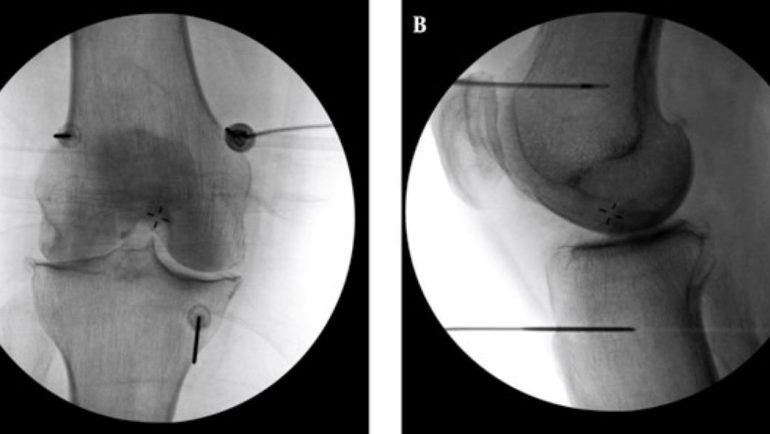方濤:《歸海》這個書名來自喬治的一次夢境:奔流向海的河流,在他的夢中是複數的,它們相遇、碰撞、粉身碎骨,然後相融,變成一條更大的河流。現實中,《歸海》這個的書名從何而來?
張翎:書中喬治的這個夢,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在寫英文版Where Waters Meet時,文稿早已完成,我卻遲遲沒想出合適的書名。有一天早上五點半,在半夢半醒的朦朧之中,一個書名突然闖進我的腦海。我怕忘記,從床上跳躍而起,赤腳去找紙和筆,把它記錄了下來——這就是後來的Where Waters Meet。這件事有點詭異,我就忍不住把它寫進了書里。後來的中文書名《歸海》,就是從這個英文書名演繹而來的。
方濤:《歸海》是你第一部用雙語寫作的作品。先有了Where Waters Meet,後又寫了中文版的《歸海》。第一次嘗試用英文寫作,感受如何?兩個版本文本內容區別大嗎?
張翎:我有過將近七年的正規英美文學訓練,用英文寫一部小說大概也不是一件特別艱難的事。但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卻一直選擇用漢語寫作,因為我覺得母語可以最貼切地表達我想要表達的情緒。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只要他的第二語言經過了足夠的訓練,是可以勝任用第二語言來架構小說情節的,但是情緒和氛圍卻是母語所賦予的一種特殊能力。用母語我可以寫出傳神的境界,而使用第二語言,我卻只能停留在「達意」的層面。
這是我首次嘗試用第二語言寫作,自然遭遇了許多挑戰。首先是語言關——這還不僅僅是詞彙量的問題。在母語里,我們選擇一個詞語時,不僅知道它的字面意義,也深知它詞底更為微妙的內涵。而在第二語言里,我們雖然瞭解詞面的意義,但對詞底那些豐富的聯想失去了精准的判斷,甚至不知道有些詞語能否構成一個統一的語言風格。要在英語中找一個傳神的說法,會比中文多花三五倍的力氣。用英文寫作的過程是一個腦子永遠在尋找舌頭的過程,有些耗神,但一旦找到,卻是妙不可言。英文詞是多音節的,能構成與單音節的漢語詞不同的節奏和樂感,這個探索過程給了我極大的興奮感。
另一個挑戰是如何用英文表述一個非英語文化習俗的概念,並在詳述和略述中間作出選擇。小說不同於學術論文,不能一味地添加註腳,因為注腳會影響閱讀的流暢感。於是我就把對背景知識的解釋,編織進故事敘述之中。這樣做的風險,是偶爾會出現一些略顯臃腫的英文句子。
我寫這部英文小說時,並沒有考慮出中文版,所以創作思路是完全以英文進行的。但寫完之後,出版社鼓勵我出一個中文版,於是我開始了《歸海》的再創作過程——它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一個部分重寫的過程。最主要的變動是背景知識的詳略重置,其次,中文版添加了一些符合中文讀者閱讀習慣的起承傳合的過渡段落,但兩個版本在故事框架和人物脈絡上基本沒有差別。
方濤:你在加拿大曾經做過十七年聽力康復師,《歸海》中袁鳳的丈夫喬治同樣從事這個職業,這應該不是一種巧合。你作為聽力康復師的經歷,是否構成了《歸海》的創作靈感?你著重突出了「戰爭溢出物」這一概念,你怎麼理解這一概念?
張翎:把我曾經的職業安在喬治身上,這就給我的寫作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一個作家在寫熟悉的生活時,自然會更有底氣。書中涉及到那些診所的場景以及與阿富汗難民阿依莎的交集,寫起來很自然,因為那就是我在診所工作時的日常。
在我的病人中,有一部分是從各個戰場下來的退役軍人,還有一些從世界各地湧來的戰爭難民。我見證了戰爭和災難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記,他們讓我思索「創傷」這個話題。戰爭和災難是事件,有開始有結束;但災難帶來的後續影響,是事件的「溢出物」(spill over),無人能預測它會在一個人身上存留多久。我偏愛我的母語文化,所以忍不住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移植」到了自己的民族歷史中。
方濤:《歸海》探討了戰爭帶給人類長久的後續影響。《歸海》是你的「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能簡單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系列嗎?從《餘震》《勞燕》開始,「戰爭、災難的創傷故事」一直是你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你覺得「創傷」本身是否有意義?如果有,是警醒還是救贖?
張翎:「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計劃,是在我寫《勞燕》時就已經產生了的。之所以叫「戰爭的孩子」三部曲而不是「戰爭三部曲」,是因為我並不旨在正面書寫戰爭,我想寫的是戰爭遺留的後續影響。這個「孩子」,可以是任何一個被創傷殃及的人,和年齡並無直接的關係。
「創傷」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戰爭和災難,創傷就無可避免。假如人們能透過災難的表層,看到潛藏的創傷,並正視創傷和修復的多種可能性,那麼,探討這個話題就是有意義的。
方濤:從《勞燕》到《歸海》,你都以女性為主角,特別關照了女性對於戰爭傷痛和恥辱的隱忍,以及她們如水般堅韌的生命力,這是你近年來創作的重點嗎?
張翎:對於女性來說,除了承受戰爭帶給人的普遍創傷之外,還要蒙受獨屬於女性的恥辱。這個恥辱除了戰爭強加的,還有社會傳統文化偏見所起的作用。這種恥辱往往是無從辯解,一生也不能擺脫的。在我們傳統的戰爭文學里,女性大多是缺席的,我想把關注點放到這群被忽略的人身上。我的女主人公把生命的氣血節省著用,在別人使用情緒的時候,她們使用耐心,她們熬過了各種逆境,是survivor。我把她們比喻成流過各種地形的污泥濁水,她們滋養他人,保守自己,是我心目中具有強悍的生命力的人。
方濤:小說中對「母親」袁春雨這一形象描述極其深刻。她以最隱忍、最低的姿態熬過戰爭的創傷,但為了女兒一次次地冒險、爆發。「母性」似乎不僅是女性力量的來源之一,也是人性最柔軟的角落。春雨在面對毫無人性的日本軍官小林時,也唯有「母親」能在他鐵石心腸中裂開一條縫隙。母親對人類跨越文明和立場邊界有著的恆久影響,不忘記母親,就不會忘記母親身後攜帶的歷史,這是你想通過小說所表達的嗎?
張翎:人類文明最大的敵人就是群體的健忘,缺失反省是人類歷史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轍的重要原因。沒有個人的遺忘,就不會有群體的遺忘。但是抵抗群體遺忘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作為一個小說家,我並不能獨自承擔起一個如此重大的社會話題。我只想盡量認真地把靈感化為可信的故事和人物,用人物來講他們的故事。袁鳳沒有在母親身後忘記母親,她沿著母親留下的蛛絲馬跡來探索母親走過的路。對袁鳳來說(可能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如此),不忘記母親就是不忘記歷史,因為母親身上攜帶著一個世紀的歷史。
方濤:你在《歸海》中說:「真相有價。一隻毀壞的蚌殼,就是珍珠的代價。」或許,現實中,我們付出殺死一隻「蚌」的代價,也可能無法獲得「珍珠」。看完小說,我內心升起一個巨大的疑惑——我們真的有能力瞭解我們最親密的人嗎?
張翎:走向「有知」是有代價的,因為這個探尋的過程是單行線,不可逆轉。一個人可以選擇蒙著耳朵,繼續過「無知」但安全的日子;也可以選擇冒險前行,打開蚌殼,尋找珍珠。毀壞的過程很疼,如你所說,即使打碎蚌殼也不能保證裡面有珍珠,甚至還有可能找到一團淤泥。但人的內心存在著好奇和探險的天性,這個天性推動著社會不斷挑戰極限、發現新的區域、拓展認知疆界。破碎和毀壞是人類為自己的探索欲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寫完《歸海》,我加倍珍惜掩藏在我們前輩身上的歷史,也深感遺憾年輕時沒有去認真探求那些本伸手可及的蚌殼——它們已經隨著親人的離去,永久消失。我們本該有能力瞭解我們最親密的人的,阻擋我們的是怯弱、懶惰、還有對一時安逸的貪求。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我們要去深深瞭解我們的前輩,他們是我們瞭解自己、切入歷史的最好入口。
張翎簡介
張翎,海外華文作家,加拿大國家文藝基金、安大略省文藝基金獲得者。代表作有《歸海》、《勞燕》、《餘震》、《金山》等。小說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年度小說家獎,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紅樓夢世界華文長篇小說專家推薦獎,曹雪芹華語文學大獎等文學獎項。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片《唐山大地震》,獲得亞太電影展最佳影片。小說被譯成多國語言。
Read More